检票 保洁 执勤 “90后”作家杜梨的园中日常
2023年8月7日,杜梨在北京接受《环球人物》记者采访。(本刊记者侯欣颖/摄)
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杜梨:
1992年出生于北京,青年作家、英语译者。先后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西湖》《花城》等文学期刊发表小说作品,2023年5月出版散文集《春祺夏安》,引发关注。
1924年11月5日,直系军阀首领冯玉祥带兵闯进紫禁城神武门,宣统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被逐出宫,此后,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开始对外开放。但彼时,内忧外患下,国库空虚,占地近300公顷的园子年久失修,花木凋零,杂草丛生,加之远离内城,游人稀少。99年后的今天,皇家园林变成旅游胜地,暑期旺季,每天都有数万人次刷闸机进园。早上6点,附近晨练的大爷大妈准时到达南如意门,十七孔桥上开始熙熙攘攘,昆明湖的游船下饺子似地离岸,佛香阁前游人如织……
“好多人!”一落座,杜梨便跟记者大发感慨,“昨儿有一研学游的队伍,差点儿挤不进来。”一口生动的京腔仿佛把人带到闹哄哄的检票现场。除了写作,杜梨的本职是公园里的一名基层工作人员,检票、站殿、保洁、指路、客服答疑,什么都干。2021年6月,她将这些工作日常写了出来,文章被京味儿作家叶广芩转发,迅速获得大量关注。“大爷大妈不停来找我,小朋友问我文章在哪里看,甚至学姐偶遇的陌生人、闺蜜在网上认识的相亲对象,都知道了。”两年多过去,园中的故事经她零敲碎打、增增补补,结集为《春祺夏安》。书里有园中老、中、青三代各色人物,有家中祖辈投身共和国核工业的历史,有啼笑皆非的俗世故事,还有沉默矗立的亭台楼阁、旁观一切的菩萨造像。
杜梨说,《春祺夏安》这一书名并不是自己取的。“春祺夏安秋绥冬宁”是传统书信的结尾语,这种传统文人气,原本让她觉得过于文艺,如今再看,她发觉文艺背后藏着别样的烟火气,“这种烟火气不是说今儿我去哪儿吃了个美食,明儿到咖啡厅写个生活随笔,而是看看浮世百态,人必须活在真实的生活里,不管在哪个时代。”
《春祺夏安》。
“什么时候也没来过你这样的”
2020年夏季,杜梨辞职“家里蹲”,刚刚考博失利的她,还未从繁重的学习中恢复过来,又要承受家人日益灼辣的目光。
一天,母亲坐在沙发上,正抱怨自己买的北京公园年票因为疫情一次也没用过,一打开公众号,看见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招聘信息。于是,强烈提议杜梨报考,“离家近,环境好,稳定又有保障,何乐而不为?”杜梨无奈,赶在最后一分钟交了报名表,经过4个月笔试、面试的拉锯战后,竟顺利入园,进了“夏宫”。
在这之前,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做这样一份工作。研究生毕业于英国,主修现代文学和创意写作专业,回国后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西湖》《花城》等文学期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,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、“《钟山》之星”文学奖……用杜梨自己的话说,做了20年“作家梦”的她选择到公园检票是“脱下落满雾霾的长衫,投入到火热的为人民服务中去”。她的同事则诧异道:“什么时候也没来过你这样的啊!”
相比坐办公室,杜梨还是低估了在园里上班的难度。每天早晨不到6点,公园检票口就排了一长串来晨练的大爷大妈,他们有老年卡,一律免票。检票口这道门一定要开得利索,如果因为各种问题,让他们的冲刺延宕了一两秒,他们就会开始不满:“怎么我天天跟这儿过都没事,就你拦我?”有人却不比速度,偏爱让检票员为自己单独刷卡,只为享受那一刹那的人工服务,听那一声电子音的问候:“请进。”
颐和园佛香阁前的台阶上游人如织。
好在更多的是体谅人的大爷大妈,心疼年轻人整日站岗,在经过票亭的时候,会突然探身进来,笑眯眯地送她一把野杏,或是打个招呼,嘘寒问暖。
进到园子里,各个大殿的值守工作也不轻松。佛香阁曾是“西太后”慈禧烧香礼佛的地方,位于万寿山前山台基上,俯瞰昆明湖、排云殿,地势高耸,阁里供奉着一尊千手千眼、铜胎镏金的观世音菩萨。在此轮岗期间,杜梨每天开阁签表,消毒拍照,拖地洒扫,偶尔提醒拾级而上的游客小心脚下。可总有人把提醒当耳旁风,她在书里幽默地写道:“通往佛香阁的台阶为100级,较为陡峭。有人痴迷于悬崖边的探戈,踩在台阶边拍照。我小碎步前去提醒,他又悬空半步,仿佛他玩的就是我的心跳。”
“夏宫”的冬天,最为难熬。为了保护古建和文物,各个宫殿里都没有现代的供暖和照明设备,一切以防火安全为原则。数九寒冬,站殿值守的人只能裹紧单位发的羽绒大衣,大衣量身定做,却必须加肥加大。“因为里面还要穿上两层羽绒、毛衣和保暖内衣,腿上穿三条裤子,脚蹬厚底登山鞋,浑身上下贴满暖宝宝,人像一座红塔山”。
他们的选择
豆瓣读书上,许多看完《春祺夏安》的读者都觉得新鲜、生动,“书的名字是岁月静好,描绘的生活却烟火气十足,是一份难得的当代百姓生活实录。”也有读者疑惑:“这么高的学历去做这些工作,不可思议。”对此,杜梨回应:“职业没有高低,每个人的选择不同而已。”相比伟岸的古建筑以及日复一日的工作,杜梨在书里写的更多的,是形形色色的同事和他们各安天命的选择。
园区工作人员在进行安保作业。
一口东北话的风掌门再过几年就退休了,早年的她是体工队的篮球运动员,转业而来,做事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。头一回带新员工上山,她翻开小黑本,让他们记了整整一页注意事项,大到如何应对游客,小到在大殿里该穿多厚的鞋。风掌门一再强调:“我们是站立式服务,不要倚靠柱子,也不要躲到菩萨身后去。”
万寿山上,只有一个人不怕冷,那就是鼬哥。在众人都开始裹紧棉袄时,鼬哥依旧穿着白衬衫,挽起袖子,在山上跑上跑下。鼬哥考过了英语专四和专八,当过英语辅导班的老师,起初很认真地做辅导教材,发现培训机构压力过大,考来了园子里。鼬哥的人生梦想是过上平静的生活——每次工作完后,鼬哥或窝在小沙发上倒头休息,或带着游戏机玩单机游戏。天气好的时候,拿一把小椅子坐在外面,对着蓝天、太阳、满山的柏树吃饭,园里的猫儿在不远处盯着他,馋得口水直流。
还有同事冰轮,年轻时一双丹凤眼,眉清目秀,神色桀骜,身边总围着姑娘。可他兴致寥寥,自小修习长号,虽早早展露出天赋,却阴差阳错得不到进修机会。后来他收起长号,来到园中,每天健身游泳,满头大汗后吃一碗面条,什么也不想,日子倒也清闲。
“有趣的故事我都写”
“身边的同事几乎都是爽利的大哥大姐,很多人之所以安然待在这里,赚着不多的钱,是因为他们有其他可以发光的领域。”就像写作之于杜梨。
1992年秋天,杜梨在海淀出生,身为“核三代”的她,却自小怕做数学题,小时候写奥数卷子,父亲紧皱眉头在一旁盯着,方程式解不出,劈头盖脸一顿教训。唯独写作文时,她下笔如有神。6岁那年,在爸爸给她念《伊索寓言》时,她决定成为一名作家,并开始大量投稿,没有发表也不放弃。长大后笔耕不辍,科幻小说、非虚构作品、京味儿文学,“只要是有趣的故事,我都写。”她说。
“我觉得‘有趣’是当代文学作品稀缺的特质。有时候跟朋友聊天,很简单的话,他们会说得非常有意思,非常幽默,我很想把这些人物、语言、故事传达出去。”杜梨说。如今,“90后”作家群体的内倾化愈发明显,过多地描写自我内心世界,杜梨避免如此。
她的文字总是充溢着一个“90后”活泼泼的趣味,她笔下的园子连接千年、横跨万里,比如这一段:新裤子有首歌叫《散步到夏宫》,“散步西郊的荒野”,唱的可能是颐和园,可能是圆明园,还可能是法国的凡尔赛宫。陈婧霏有首歌叫《夏宫》,的确唱的是颐和园。骆集益有首曲子叫《秋瑟的颐和园》,听起来很凉快。还有一首曲子叫《颐和园华尔兹》,采样阮籍三拍的《酒狂》,加入西方的华尔兹,有古琴,钢琴和单簧管,听起来愉悦至极。
杜梨写了不同人的人生故事和人生态度。“这本书里的每一代人都有一种饥饿感,我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那辈吃不饱饭,我们这代人过了温饱到小康了,但灵魂上还是焦虑,还是需要安全感。”文学评论家孙郁给了她很高的评价:在伟岸的古物面前,一批新式青年内心的觉态,那么美地闪动在古老的空间里,让我们忽地感到,寻常人的精神原也并不低矮。
故园无声迎来送往,过客、游客,久驻、暂留,杜梨渐渐发觉“有些东西是弥足珍贵的”,可以让人穿透浮世喧嚣,获得平静。她想起冬日的一天早上,独自去佛香阁顶层掸尘,拿着鸡毛掸子,蹬于亭台之上,扶栏眺望,手边就是千佛琉璃,浅黄、青瓜绿和柔紫的光彩温润清凉,再望一眼远处的昆明湖,水面泛着金色的光。站在高处,阳光将身体晒得暖洋洋的。“我总想到空中楼阁这个词,甚至觉得在这阁楼外可以再待一百年,静坐观山,读书打坐,喝咖啡喝茶。”
标签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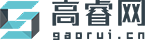



 4对双胞胎考入武大!她们是最酷的“学习搭子”......
4对双胞胎考入武大!她们是最酷的“学习搭子”......
 故宫雨花阁为何不对游客开放?只因这有三样宝贝,让游客红了脸
故宫雨花阁为何不对游客开放?只因这有三样宝贝,让游客红了脸
 沪铜日内震荡走强 市场人气受振回暖
沪铜日内震荡走强 市场人气受振回暖
 凤凰股份:8月21日融券卖出2000股,融资融券余额1.78亿元
凤凰股份:8月21日融券卖出2000股,融资融券余额1.78亿元
 美国商务部将27个中国实体从“未经验证”清单剔除
美国商务部将27个中国实体从“未经验证”清单剔除
 惠普6535b开不了机怎么办 惠普6535b开机黑屏
惠普6535b开不了机怎么办 惠普6535b开机黑屏
